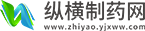朱一龙,你真以为自己能捂住观众的嘴?
现在明星这么能捂嘴了?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说你啥了,心虚成这样?
亏得还夸你,真让我感觉到恶心。
以下为原文:
昨天看了《消失的她》,来写一下朱一龙。预警一下,非粉非黑非广告。
先说观点:
朱一龙是当下同年龄段男演员里最有潜力成为top1的男演员,但是现在还差点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我需要先岔开话题,聊到我曾经写过的一个男演员,他是韩庚。
我曾专门写文章说过,韩庚是非常有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演技派演员的,他的上限可以很高。(我打赌这「前顶级流量」将是下一个演技担当)
我当时的论证是以《前任3》和一些已经公映的作品来举例说明的,很多人当时都怀疑我收了他的钱夸的,实际上并没有,当时我的这个判断来自于我私下观看了一部他参演的作品,叫《闻烟》(未公映)。
在那个作品里,他演绎了一个质朴叛逆的男孩的成长过程。
我之所以因为这个片子指出他的潜力,并不是因为他演得牛逼,而是我嗅到了他身上仍保存着的一些独特的个人特质,例如坚韧等等。
我看演员,是看可能性的。
在我看来,个人特质,比演技还要本原。
因为个人特质这种东西,它完全来自于演员私人的经历,只有它才是导演去指挥演员的舵,它并不属于“演技”的范畴,但是会直接构成演员的“表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特质,你曾喜欢过的人,或者曾挨过的打,各种各样的久远的事情,都有可能导向你身上生长出一些专属于自己的特质,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演员,但是如果从职业化角度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使用自己的个人特质来创作“丰富”的角色。
这就是素人演员跟职业演员的根本鸿沟。
某些特别善于使用素人演员的导演,眼光都是非常毒辣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往往就是将素人演员松散的个人状态,聚合成一种有的放矢的角色力量,进而服务于影片。
在影片《无人知晓》中,是枝裕和就是通过将当时年仅14岁的演员柳乐优弥推上了戛纳影帝的宝座,当年的最佳女主,正是张曼玉(《清洁》)。
你能因此说柳乐优弥的演技有多好吗?并不能,但是换一个演技比他好的就能呈现得比他好吗?也不能。
这就是演员的个人特质的强大。
郝蕾的《颐和园》,章子怡的《一代宗师》,成就她们的都并不是她们念叨个没完的演技“技巧”本身,而正是在导演金手指下的个人特质的光芒四射。(但是咏梅和王景春的《地久天长》却是实打实地凭演技拿下的桂冠,感受一下区别)
所以我当年那篇文章的意思是说,拮据的少年时代和无情的练习生生涯,在韩庚身上留下了很多“普通人的历史”,这些“普通人的历史”里面的坚韧的力量,在大量的角色身上都具有强烈的普适性,运用得当非常容易一飞冲天,因此,我认为韩庚是非常有可能出作品的。
那么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作品来呢?
因为还有一个残忍的事实是:
个人特质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唯一条件和绝对稀缺性资源。
对于大演员来说,真正的稀缺性资源是有观众缘的皮相和个人强烈的职业追求。
皮相不多说了,有的都有,没有的说了也没有。
说一下职业追求这块。
演员的职业追求它具体体现为:
① 渴望机会;
② 珍惜羽毛;
③ 意志坚定。
就这三点。
需要注意的是,强烈的追求带来的渴望与珍惜,通常并不是外放的情感,它并非会导向疯狗般的热烈抢戏——
强烈追求的表现,是高度凝结的专注。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演员火的那一两部作品总是特别好,之后的作品却慢慢有点跟不上,因为不专注了。例如章宇,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而相对应的,有些人演技起初并不精彩,但是在后续却能一路高度猛进,独此一家。比如吴京、赵丽颖都非常说明问题。
有观众缘的皮相吸引观众,有追求的职业选择和优质的职业呈现留住观众——
同时,越来越坚实的观众基础又托起演员的商业价值。
这就是过去几位商业价值巨高的大花都立足于演员这一工种的原因:
演员的职业生命会随着角色的成功而得以不断延长,并以此抵消掉商业和负面给他们带去的诸多消耗。
经典的角色,就是演员取之不尽的血包。
朱一龙现在差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经典角色”的内在支撑。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演员,但是每次看完他的戏,又觉得他在表演上的思路还没有完全打开。
这一点,在《消失的她》里面就非常明显。
在这部影片里,朱一龙的演技评价两极分化。
有些人认为他的表演充满了细节,有些人则认为他用力过猛。
实际上这些不同的感受都是成立的,因为何非这个角色塑造得确实很割裂。
这种割裂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何非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较为摇摆,没有为人物充分建立起一个统一且无懈可击的内核。
结合影片,我具体一点说一下。(以下内容含剧透)
朱一龙所扮演的角色何非,深陷赌债,在潜水馆里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李木子(黄子琪 饰),因为李木子出身显赫,所以何非与同事一起设下圈套,诱发李木子的圣母心,骗钱骗色,最后甚至设下严丝合缝的圈套在东南亚要了李木子的命。
这个设定下的何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因为他的决定都是“只求利己”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必须抓住他的性格成因的来创作,即——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这也正是朱一龙站在演员角度需要着重处理的地方,即:
赌性是如何使人逐渐癫狂的。
它需要强调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朱一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处理“何非已经癫狂了”这一个结果上。
对此,他做了非常多处理,例如脸部抽搐、牙关不受控制地开合、行动狂躁,等等。
这一切都是很用心的演绎,但问题是,它是一个结论,一个“何非就是一个坏人的”粗暴结论。
观众直接就看到一个男人集诈骗、赌博、凶杀、愚蠢于一身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如果不进行细节性描写来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观众是一定没有办法真正接受他的(“他”不等于演员哈)。
它给人的感受并不是演员诠释了一个坏人,而是如同这个坏人的直接出现一样,直接排斥这个坏人。
因此,如果忽略思路,直接处理细节,演员再怎么去处理,都只是一个对结果的处理,费力不讨好。
那么,到底要怎么从表演上拆解何非这个人物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单纯的赌博行为不会使人“生病”,真正使人生病的是赌博这一行为带给人们的心理刺激和认知紊乱。
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何非是一个来大城市混饭吃的打工仔,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三五千,但是一局五分钟的赌博却能让他随便就进账三五千、十几万,这比他过去一辈子见过的钱还多,换了是任何人,价值观都必然遭受重大冲击!
他一定会想:
“在这里,钱的来去都那么容易,那我以前的努力又算什么?!”
所有的赌徒,都会由此发现,用劳动去换取回报,是一件效率极其低下的事情,一输一赢之间,他们就变了——
统一变得不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是开始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因为,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不公平”的。
为什么对于有的人来说,钱就能来得这么容易??何非不理解。
这种“不公平”的感受,在他遇到家境显赫的李木子之后,再次被强化了。
如果说赌场上的赢家钱来得容易,多少还需要靠实力(下注)的话,那么像李木子这种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拥亿万家财的人的出现,简直就是对何非的凌迟。
凭什么啊?
价值观已经被反复冲击且内心力量并不足以消解这一问题的情况下,何非的心态开始畸变:
他必须去与魔鬼做交易!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愉悦,感到公平,感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比起钱,这种感觉才是真正让人上瘾的东西。
这种交易,一旦开始,根本不会停,因为它的机制是,赌徒幻想着自己是一个已经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在用一种聪明的方式,在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过去自己付出努力去寻求回报的这种行为。
它是一种心理代偿。
只是,问题在于,何非们逐渐发现:
越想掌控,越没法掌控;越没法掌控,越想掌控...
这一点,才是何非这种越穷越赌的赌徒走火入魔的原因。
对此,朱一龙是需要有演绎的。
这种演绎甚至不需要改动全片,我们只要在三个关键节点植入这个意识,那么人物就会脱胎换骨。
这三个关键节点分别是:
1、第一次见到李木子时;
2、陈麦(倪妮 饰)不断地怀疑他时;
3、得知李木子死的时候怀有身孕时。
逐一来说一下。
第一个节点:
第一次见到李木子的时候,何非深陷赌债危机,他此时还没有真正地丧心病狂。所以当他把李木子救起时,他的反应得是平淡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一开始就觉得他是自己的一道光之类的。
这很假。
因为此时在何非的心里,她与自己无关。
这种“与自己无关”的感受是需要表达出来的。
只有表达出这种“无关”,才能体现何非本性的善良(救了她一命)和本能的功利(因为钱而捕猎她),才能更有效地体现出何非的内心状态,此时还不是绝对的恶。
第二个节点:
在车上陈麦不断地质问他的时候,何非直接下车表现出强烈的愤怒。
事实上,这是何非在整个求助陈麦的过程中,唯一一次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对陈麦的愤怒。他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俩的关系又无法真正成立,因为:
难道心思缜密如何非,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陈麦吗?
在经典电影《风声》里面,黄晓明扮演的日方势力武田,在电影的前半段一直与李冰冰所扮演的李宁玉和平相处,但是因为一直查不出间谍“老鬼”,所以武田开始怀疑李宁玉,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猜想,他对李宁玉进行了搜身处理。
当年李冰冰就是通过这个角色打败周迅等人,勇夺金马。黄晓明虽然后期演技被诟病很多,但是这个角色、这一段戏,却一直被奉为经典。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演员在这一场戏里面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力量——
李宁玉方是维护正义的力量,武田方是服务邪恶的力量——
被呈现得惊天动地、无可挑剔。
他们是怎么做的?
黄晓明扮演的武田把自己的怀疑的情绪减到了最低,反而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李冰冰扮演的李宁玉则把自己的恐惧调到了最高,让人代入了她彼时的未知;且二人始终都在不断抑制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的流露,而不是生怕观众看不出来自己在干啥——
这种抑制,才符合人在极端条件下的真实反应。
说回何非和陈麦的对立,是不是就感觉空空荡荡了很多?
一个吼一个,一个再吼回去。谁看得出你们性命攸关?
如果何非真的是一个赌红了眼的杀人犯,那么他遇到问题的最主要状态大概率并非愤怒,而是冷漠。
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牺牲其他人的冷漠。
这,才能把何非推向寒冷的极致。
第三个关键节点:
得知李木子怀有身孕的时候。
在这里,何非的表演是痛苦而悔恨地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意图,但是这个表演算是真正自己摧毁了何非这个人物。
为什么?
因为它在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孩子比大人重要。
只有孩子能让罪犯觉得悔恨,而活生生的爱人,说死就能死。
且不论这个观点的对错,但是它一定会在无形中传递出这种价值观,这是让人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就会非常不舒适的,同时从角色的角度,也让何非这个角色显得很搞笑,你杀妻都能随便决定,现在在这哭一个没出生的孩子,装什么大尾巴狼呢?是吧。
但是,如果朱一龙在这里稍微改变一下思路,这个地方的质感,会大不一样。
那就是,他可以用“苦笑”去代替“痛哭”,用“解脱”代替“悔恨”去处理。
什么意思?
很简单,因为何非的一生,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一生。
他小时候吃物质窘迫的苦,有钱了之后又吃价值观打架的苦,他始终是处在一个很自卑很孤独的状态中的。
当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孩子时,他当然也会很惊讶,很后悔,但是!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站在何非的角度想,如果我觉得人间不过就是炼狱一座,那么我真的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来这炼狱经历一番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何非自己对于“活下去”,就没有那么多的眷恋,所以他在得知李木子是带着孩子一起走的时候,终于感受到了命运的讽刺和内心的无力再一次席卷而来?
还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啊。
那种“不公平”的感觉。
那种“越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越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感觉啊。
至此,这个人物是不是就能在这个思路的改动下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呢?
何非,一个失败的反抗者,一个无力的下等人。
这,将成为何非的注脚,让他在观众心中的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这就是“表演”所能做的事情:
用创作者的思想入侵观看者的思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意念之间。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就差不多了。
很多不懂表演的人会习惯性地提出,xxx是剧本的问题,xxx是导演的问题,等等。
对,你们说的都对,演员表演的最终呈现,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左右的,它有太多的因素在作用。
但是这跟我上面说的没有任何矛盾。
因为,高手的高明往往就在于能够突破更多条件的限制。
换句话说,大家都面临很多限制,但是你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这条路,就属于你!廖凡在《邪不压正》中的例子我说了好多次了。
这篇文章比我之前很多文章都写得长,写得细,确实也是我想把我对于一个演员的正面期待与客观问题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整理。
我自己确实在朱一龙的表演里看到了很多东西。
很多跟演技关系不大,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东西。
我会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闷声燃烧的劲儿,他并不让我觉得像娱乐圈大部分已经成名的艺人那么功利,相反,他似乎是真的往山峰最高处发起冲击,有着更高的追求和理想。
我不知道其他观众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看到他在何非这个角色身上表达出的很多愤怒。
他的这种愤怒让我想到好多年前采访雷佳音的时候,他曾经反复表达过的,
“我从不在现实生活里反抗,因为没用。我永远在角色里面反抗”。
我认为朱一龙亦有此心气。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说的个人特质的部分了。
那是一种昂首挺胸、无需声张的“斗志”。没有声儿,但是存在。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许它时而会显得用力过猛,或者不够精确,这都是正常的,没关系。
成长就是这样令人沮丧和枯燥。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理想从不离开有理想的人。
在寂寞的路上遥遥地看见还有其他人也在沉默地走着,有时候甚至比抵达终点更让人觉得快乐。
希望我表达清楚了。
:)
更多相关明星演技盘点,搜索公主号:宋雯婷(id:swtstory)
标签:
推荐文章
- 深圳2021年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6530套 获得督查激励
- 研究人员最新发现 单个细胞可同时处理成百上千个信号
- 长期暴露在光照下性能退化 科学家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最大缺陷
-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 创新升级模拟训练器材
-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毕业学员综合战术演习现地备课工作圆满完成
- 宁夏启动双百科技支撑行动 构建高水平产业创新体系
- 区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屏山以“3+”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工作
- 国内首颗以茶叶冠名遥感卫星 安溪铁观音一号发射成功
- 激发创新动能促进产业发展 无锡滨湖走出产业转型“绿色”路
- 走近网瘾少年们:他们沉迷网络的病根何在?
- 节后第一天北京白天晴或多云利于出行 夜间起秋雨或再上线
- 走访抗美援朝纪念馆:长津湖的寒冷,与战斗一样残酷
- 绥化全域低风险!黑龙江绥化北林区一地调整为低风险
- 农业农村部:确保秋粮丰收到手、明年夏季粮油播种
- 中国故事丨“沉浸式”盘点今年的教育好声音!
- 升旗、巡岛、护航标、写日志,他们一生守护一座岛
- 他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重装空投“兵专家”
- 获2021年诺奖的蛋白,结构由中国学者率先解析
- “双减”后首个长假:亲子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
- 天山脚下,触摸丝路发展新脉动
- 且看新疆展新颜
- 《山海情》里“凌教授”的巨菌草丰收啦
- “双减”出台两个月,组合拳如何直击减负难点?
- IP类城市缘何吸引力强?玩法创新带动游客年轻化
- 面对婚姻,“互联网世代”的年轻人在忧虑什么?
- 沙害是自然界的恶魔,而他是荒沙碱滩的征服者
- “辱华车贴”商家及客服被行拘,处罚要不放过每一环
- 网游新政下,未成年人防沉迷的“主战场”在哪?
- 160万骑手疑似“被个体户”?平台不能当甩手掌柜
- 报告显示:这个国庆假期,粤川浙桂赣旅游热度最高
- 陈毅元帅长子忆父亲叮嘱:你们自己学习要好,就可以做很多事儿
- 北京国庆7天接待游客超861万人次 冬奥线路受青睐
- 从1.3万元降到700元,起诉书揭秘心脏支架“玄机”
- 都市小资还是潮流乐享?花草茶市场呈爆发性增长
- 国庆主题花坛持续展摆至重阳节
- 警方查处故宫周边各类违法人员12人
- 云南保山:170公里边境线,4000余人日夜值守
- 线上教学模式被盯上,网络付费刷课形成灰色产业链
- 全国模范法官周淑琴:为乡村群众点燃法治明灯
- 嘉陵江出现有记录以来最强秋汛
- 中国科技人才大数据:广东总量第一,“北上”这类人才多
- 神经科学“罗塞塔石碑”来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大脑细胞图谱
- 多地网友投诉遭遇旅游消费骗局,呼吁有关部门严查乱象
-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海南海口三港预计停运将持续到10日白天
- 农业农村部:确保秋粮丰收到手、明年夏季粮油播种
- 广州10月8日至20日对所有从省外来(返)穗人员实施核酸检测
- 辽宁省工信厅发布10月8日电力缺口橙色预警
- 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 10月7日、8日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停运
- 这场红色故事“云比拼”,穿越时空为我们指引方向
- 陕西支援14省份采暖季保供用煤3900万吨
- 汾河新绛段发生决口
- 看,生机勃勃的中国
- 百闻不如一见——北京大学留学生参访新疆
- 新疆霍尔果斯市2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 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88小区将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 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 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国庆5.15亿人次出游,你咋过的?
- 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61.1万人次
- 山西平遥消防4天29次救援:拖着腿走路也要完成任务
- 新疆兵团可克达拉市:195名密接者已全部隔离医学观察
- 国庆假期中国预计发送旅客4.03亿人次
- 公安部交管局:国庆假期日均出动警力18万余人次,5位交警辅警牺牲
- 国庆假期中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
-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9千米
- 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 气温将下降4℃至6℃
- 2021年MAGIC3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落幕
- 国庆假期广西累计接待游客逾3611万人次 实现旅游消费272.41亿元
- 新疆伊犁州:妥善做好滞留旅客安置返回工作
- 新疆霍尔果斯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属德尔塔变异株 未发现高度同源的基因组序列
- “数说”杭州无障碍改造:触摸城市“爱的厚度”
-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广东将暂别高温天气
- 浙南沿海村村发展有妙招 搭乘共富快车打造“海上花园”
- 世界第一埋深高速公路隧道大峡谷隧道出口端斜井掘进完成
- 直径2米“面气球”亮相 山西首届“寿阳味道”美食大赛启幕
- 厦门同安区四区域调整为低风险 全市无中高风险地区
- 哥伦比亚遇上广州:洋茶人“云上”喫茶 传播中国茶“味道”
- 新疆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1名无症状感染者为餐饮从业人员
- 中国国庆假期出行热:数字改变“关键小事”
- 添加陌生人为好友 内蒙古两女子被骗126万
- 南沙港铁路国庆假期不停工 力争今年年底开通
- 新疆霍尔果斯两例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均属德尔塔变异株
- 哈尔滨一地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
- 哈尔滨市学校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 受热带低压影响 琼州海峡北岸等待过海车辆排长龙
- 铁路迎返程高峰 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79趟高铁列车
- 铁路人国庆雨中巡查排险记:一身雨衣、一把铁锹保安全畅通
- 水能载物亦能“生金” 浙江遂昌山村以水为媒奔共富
- 科学拦峰错峰削峰 嘉陵江洪水过境重庆中心城区“有惊无险”
- 山西解除持续近90小时的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 安徽黄山国庆假期迎客12万余人 旅游市场稳步复苏
- 从进“培训班”到看《长津湖》
- 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清零 撤除离厦通道查验点
- 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创1966年以来最高纪录
- 杭州“十一”假期后初中取消统一早读